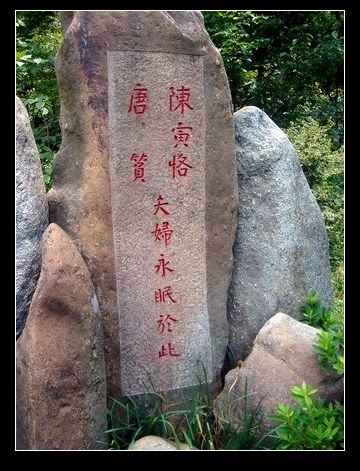春暖花開。
寒冬遠去。
暖烘烘的陽光。
讓樹木吐出嫩綠。
經過維園。
方知「花展」迫在眉睫。
又是拈花惹草好時節。
↑紅桃大展。
↑綠傘好遮陽。
↑藍蝴蝶。
↑維園的鴿子。
↑楓樹顏色「大執位」。
↑綠肥紅瘦。
↑紅綠對壘,未紅先驕。
↑密鑼緊鼓迎花展,維園。
↑維園花展,開檔在即。
↑維園室內泳池。
↑銅鑼灣,興發街。
↑北角,英皇道,國都廣場。
↑桃花源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桃花源獵艷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桃花,蜜蜂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花蜜睇真啲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蓮花山公園,深圳福田。
↑蓮花山,深圳福田。
↑大樹好乘涼,蓮花山,深圳福田。
↑樹蔭下,蓮花山,深圳福田。
↑關山月美術館,深圳福田。
↑關山月美術館,深圳福田。
↑四手聯彈,銅塑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四手聯彈,銅塑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音樂廳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音樂廳,深圳福田,書城。
寒冬遠去。
暖烘烘的陽光。
讓樹木吐出嫩綠。
經過維園。
方知「花展」迫在眉睫。
又是拈花惹草好時節。
↑紅桃大展。
↑綠傘好遮陽。
↑藍蝴蝶。
↑維園的鴿子。
↑楓樹顏色「大執位」。
↑綠肥紅瘦。
↑紅綠對壘,未紅先驕。
↑密鑼緊鼓迎花展,維園。
↑維園花展,開檔在即。
↑維園室內泳池。
↑銅鑼灣,興發街。
↑北角,英皇道,國都廣場。
↑桃花源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桃花源獵艷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桃花,蜜蜂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花蜜睇真啲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蓮花山公園,深圳福田。
↑蓮花山,深圳福田。
↑大樹好乘涼,蓮花山,深圳福田。
↑樹蔭下,蓮花山,深圳福田。
↑關山月美術館,深圳福田。
↑關山月美術館,深圳福田。
↑四手聯彈,銅塑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四手聯彈,銅塑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音樂廳,深圳福田,書城。
↑音樂廳,深圳福田,書城。